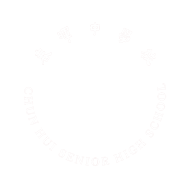闲适的天空
周一农
踏春,如今已算不得啥新鲜事儿了,海边山里,塞北江南的,可像白马湖这样,集繁荣和恬淡于一身的,则并不多见。
一
几天前,群主在群里说,想去白马湖采风,问大家如何?或许近在咫尺吧,这么些年了居然没想到去,以至每每问起,我都挺尴尬。如今能有这么个机遇,手指一点便答应了。
烟雨中起的早,车也不快,景还那么乖巧,原本让机会激起的那点兴奋,不一会儿便又迷糊回去了。
出了驿亭口地道,色彩的旋律渐渐变得爽活起来,一边是接地连天的油菜黄,过了一片,又上来一片,让你无须盼望,无须期待,春的脚步便已经来到眼前;另一边呢,则是倒映山色的镜面绿,估计没谁家相机的镜头能有它大和清晰。下车沿湖走了不一会儿,过了马鞍桥,便进入了那个期待中“春晖名人文化带”。这里三面环山,一边面湖,如此地理格局,的确内锁宁静,外御尘嚣,难怪经亨颐要把校址选在这里。“是白鹭!”此时,眼尖的发现,对面的山脚下忽隐忽闪亮起了星星点点,兴奋道,在这样的树丛里,白鹭群是很抢眼的。湖心一只小船也缓缓地朝这边飘来,只见随意,不见艄公,犹如一缕悠悠的仙韵。
真是一个难得的好天。因为雨后,空气格外洁净,油菜花的灿烂也比往日收敛了一些,照说,江南是没人不爱春日暖阳的,可不知怎的,我却不喜欢春光下的油菜花:太艳也太暴力。印象最深的一次,是在江西婺源。晴了几天,本已春暖融融,可车子还是把我们带入了万亩油菜地,闹得眼里眼外“满城尽带黄金甲”,没一会儿就出汗了。当时才孟春,我们却都以为夏天的影子就已在身边了。所以,看着眼前这片黄花,不禁默默感谢起清晨的那阵细雨来。更难得的是,因为双休,春晖的孩子也回家了,于是,周边安宁得让我很自然地想起了朱自清的那句话:
春晖是在极幽静的乡村地方,往往终日不见一个外人。(朱自清《春晖的一月》)
不过,那天的事实却是,除了我们这群外人,几乎没见一个本地的。
二
自上世纪初,那群人在此集结,人们心里便多了一个以白马湖命名的文学的天空。后人仰望这一段时,总爱拿它“清淡”而“宁静”的风景来说事儿。可来了后我却觉着,那几个词都不如80年前朱自清那个“闲适”来得左右逢源,那些视角至多不过“闲适”的一个注释。当然,疏朗、隽秀、深邃这些侧面也很好地丰富了白马湖的闲适,让我们的眼光多了几缕文化的细腻。
从水泥丛林中来到这里,天一下子高了,蓝了,云也淡了许多,几幢保存完好的名人故居背山面湖,夏丏尊的平屋、丰子恺的小杨柳屋、经亨颐的长松山房以及李叔同的晚晴山房等等,每幢都间隔几步、几十步有致地排列着,让人觉着,它的疏朗是宽容的一种别称。字面解吧,“闲”是指时间盈余,而“适”说的是空间阔绰,的确,如果逼仄了,人就容易心浮气躁起来;看风格呢,那边,春晖的新楼和旧居安然参差着,眼前,西洋的、日本的、本土的,各种建筑的风格土洋搭配着,看看春晖的精致,再瞅瞅那些平屋的粗疏,还能感到一种文野的唱和,嫌不够的话,你还可细看山边一楼,那几竖超长的百叶窗散发着十足的欧陆风情,而黛瓦粉墙则明显地连接着江南的地气,如此兼容恐怕该是白马湖才有的一种气度吧?
它的隽秀是一种气质,上上下下的。朱自清当年的感受是:
山是青得要滴下来,水是满满的,软软的。小马路的两边,一株间一株地种着小桃和杨柳。小桃上各缀着几朵重瓣的红花,像夜空的疏星。杨柳在暖风里不住的摇曳。(朱自清《白马湖》)
没想到这么些年过去还这样。那天来时正赶上雨后,桃红和杏白都有些疲惫,草的世界却绿得正闹,那些过了冬的倒也绿得平静,每颗顶上的那一两片嫩鹅黄却不安分,正调皮地探个脑袋出来透气,就像小鱼苗嬉戏在碧水间一样。虽说我没见过高原草甸中活的虫草,可我能想象它们的复活也不过眼前这般情景。那天不巧,大师故居的门没一扇是开着的,可透过那些围墙的雕檐和花窗,我就知道,它还是没把隽秀关住。再看看那矮矮的小杨柳屋,跟边上的树一般高,也有的树比它还高,可它的味道老让人想起屋主人的漫画,《人散后,一钩新月天如水》。朱光潜曾评价说:“造境着笔都不求奇特古怪,却于平常中寓深永之致。”这是在评画,也是在评房子。
其实,并非所有的江南山水都闲适,有人甚至这么说:
白马湖的山水和普通风景地相差不远,唯有风与别的地方不同。(夏丏尊《白马湖之冬》)
正想着,边上有人说了,电视剧《围城》的三闾大学就是从春晖里取的景,这让我一下子回到了那秀润的长廊和细密的雕栏。那还是80多年前,一群知识青年从天南海北来到这里,传播文化,教育救国,在此,他们创造了他们人生乃至中国文化的许多个第一。正是这样的激情给白马湖注入了文化的灵气和活力。要再上溯到东晋,离此不远的东山,还是谢安与王羲之、孙绰、支遁、许询等名流“出则渔弋山水,入则言咏属文”的地方;到了南朝,谢灵运辞了永嘉太守,隐居这一带,还以山水诗名重朝野,开宗立派。不过,今天的人似乎有些淡忘了。可朱自清没忘,他的《题石鼓图》一诗,明显的用了当年的典故。
可见,地灵是因为人杰。来这儿的人,观光也罢,采风也罢,特地赶过来当解说的李老师还说我们是来朝圣的,其实朝圣也罢,都是奔的这一段历史,奔着它的深邃和成就。
可我在想,当年大师们来的时候,又是奔的什么呢?
三
读过《春晖的一月》,都知道白马湖的三件礼物:美、真和闲适,我最看重的是这份闲适。因为“美”和“真”也许可以通过教育获得,而“闲适”则只能靠山水来陶冶。只是没有想到白马湖的闲适曾改变过朱自清的文风:
当他感受到春晖的“惊异”时,已开始了名士气和平民本位的两种文化因子的碰撞,而当他要补救他的“单调”和调和他的“繁嚣”时,则开始了向平民本位文化的自觉回归。(王晓初《论“白马湖文学”现象》)
说得也是,虽然郁达夫说过:“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,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那一种诗意。”可我一直觉得他首先是散文家,尔后才是诗人;而且,他的散文,尤其是早期散文,像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、《绿》等,不缺美,也不少真,可闲适却不富有。行文小小心心,措辞女声女气,处处散发着淮扬的甜韵。其实,他的诗不如散文,所失也就在闲适。
我曾不止一次地到过扬州,也常常会联想到古城里的安乐巷27号,那是朱先生的故居,一座落寞的江南小院;联想到瘦西湖边的微澜细柳、二十四桥上的暖风烟雨和清炖狮子头的粉甜松软;甚至康乾下江南时天上的融融月色、阑珊灯火和地面的玉树琼花、人影衣香,虽然不讨厌苏菜,但这样的雍容和丰腴,我还是觉得有些腻了。晓初兄说的没错。
回家后,又陆续补了些功课,我发现,白马湖还真是一只看不见的手,悄无声息间把许多东西都变得闲适了。先看朱自清吧。虽写的是同一个地方,后来的《白马湖》就比《春晖的一月》要少了些城里人的娇柔。这种影响也反应在世界观上:
我是在狭的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,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,我现在住在繁嚣的都市里,我要以闲适的境界调和它。(朱自清《白马湖》)
如果要说到夏丏尊的《白马湖之冬》和丰子恺的《杨柳》,以及该流派中的其它作家,他们散文中的那种宽松裕如、闲适自在比起朱自清的还要更洒脱一些,他们不仅能从狭狭的煤屑路中感受清新的趣味,也能从寒风怒号里听出萧瑟的诗情:
松涛如吼,霜月当空,饥鼠吱吱在承尘上奔窜。我于这种时候深感到萧瑟的诗趣,常独自拨划着炉灰,不肯就睡,把自己与以诸山水画中的人物作种种幽邈的遐想。(夏丏尊《白马湖之冬》)
于是我想,不论“立达”、“开明”,他们后来叫了什么名字,只有这才是白马湖散文得以集聚的精髓与奥秘吧?
因为有熟人,中餐得幸在学生餐厅里蹭了一顿,我要的是一份盖浇饭,“土豆牛肉”加上“青椒干丝”。尽管天下的食堂饭大同小异,大概是因为那种恬静和素朴,我们还是品出了别地儿没有的宽松与闲适。